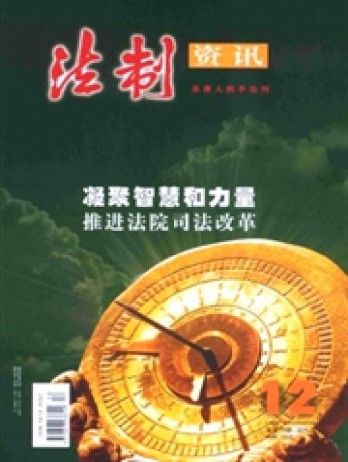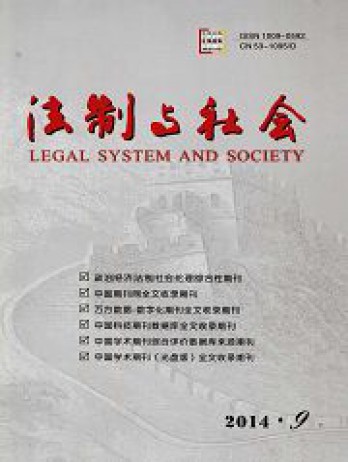法制史論文精品(七篇)
時(shí)間:2023-03-21 17:08:45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dá)。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nèi)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lái)了七篇法制史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guò)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chuàng)作。

篇(1)
俞榮根教授是我國(guó)著名法學(xué)家,1943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諸暨市。1967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1979年考取西南政法學(xué)院法學(xué)研究生,1982-1997年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學(xué)(原西南政法學(xué)院)。1993年起歷任西南政法大學(xué)法學(xué)研究所所長(zhǎng)、研究生部主任、副校長(zhǎng)、校黨委常委,1997年11月調(diào)任重慶市社會(huì)科學(xué)院院長(zhǎng)、黨組書記,并任重慶市人民政府發(fā)展研究中心第一副主任(常務(wù))、《改革》雜志社社長(zhǎng),兼任重慶市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系列高級(jí)職務(wù)評(píng)審委員會(huì)主任委員等。1998年任中國(guó)人民第九屆全國(guó)委員會(huì)委員。2003年1月,在重慶市人大二屆一次會(huì)議上選任為市人大常委會(huì)委員(駐會(huì))、市人大法制委員會(huì)主任委員。主要社會(huì)兼職有:曾任南開大學(xué)、北京大學(xué)等校兼職教授;現(xiàn)任上海大學(xué)、同濟(jì)大學(xué)、香港城市大學(xué)、重慶大學(xué)、西南師范大學(xué)等高校兼職教授;兼任中國(guó)孔子基金會(huì)理事及其學(xué)術(shù)委員、中華孔子學(xué)會(huì)理事及其學(xué)術(shù)委員、中國(guó)法律史學(xué)會(huì)常務(wù)理事、中國(guó)儒學(xué)與法律文化研究會(huì)副會(huì)長(zhǎng)等。
2005年我在西政課堂上見(jiàn)到俞榮根教授之前,已經(jīng)讀他的書近十年,是他堅(jiān)定的“粉絲”了。
1990年代中期讀本科時(shí),我閱讀的有關(guān)中國(guó)法律史論著中,俞老師的《儒家法思想通論》(以下簡(jiǎn)稱《通論》)印象最深刻。這本書中,俞老師提出儒家法文化的特質(zhì)是倫理法,先秦儒法之爭(zhēng)并非人治和法治的對(duì)立,禮不能比附為自然法,最早公布成文法不是“鑄刑鼎”,孔子也并非是反對(duì)成文法等新觀點(diǎn)。由于站在法哲學(xué)的高度并且論證嚴(yán)密,該書對(duì)中國(guó)法律思想史學(xué)中的核心問(wèn)題和研究方法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和澄清。書出版后好評(píng)如潮,連《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國(guó)際儒學(xué)》等都發(fā)表書評(píng)予以推介。聽(tīng)陳濤教授說(shuō),西政80年代出了兩個(gè)“圣人”,一是研究孔圣人思想的俞榮根,一是后來(lái)成為新儒家代表的蔣慶。
通過(guò)閱讀《通論》和之后出版的《道統(tǒng)與法統(tǒng)》,我雖未和俞老師謀面,但已非常仰慕其學(xué)術(shù)成就,知道他由于對(duì)儒家法思想開拓性的研究以及一系列富有創(chuàng)見(jiàn)性觀點(diǎn),在法學(xué)界和儒學(xué)界享有崇高的學(xué)術(shù)地位,成為西政具有全國(guó)乃至世界影響的學(xué)者。
西政精神吸引青年學(xué)子去深造
2003年我在復(fù)旦法學(xué)院進(jìn)修法律史研究生課程。王志強(qiáng)教授拿出一本俞老師剛剛贈(zèng)送他的新書《景凡文存》讓我閱讀。這是俞老師為其已故恩師楊景凡先生編的文集。景凡先生晚年拿著放大鏡閱讀了中西方大量的經(jīng)典著作,寫下了大量珍貴的文稿,但因?yàn)樽髡咭暳υ颍芏辔淖蛛y以辨識(shí)。楊先生故去后,俞老師接手這些手稿,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放下自己的學(xué)術(shù)著述,夜以繼日地整理校勘這些文字,在導(dǎo)師逝世一周年之際印制了《景凡文存》。
通過(guò)閱讀《景凡文存》,我從仰慕俞老師,進(jìn)而了解到“西政精神”。俞老師將西政的學(xué)風(fēng)學(xué)統(tǒng)總結(jié)為:高度的歷史責(zé)任感、強(qiáng)烈的憂患意識(shí);厚德愛(ài)才、重情重義、師生親如父母子女、相敬如知己朋友;創(chuàng)新精神、批判精神和學(xué)術(shù)寬容精神;嚴(yán)謹(jǐn)扎實(shí)、精益求精的學(xué)風(fēng)等。2004年我以朝圣者的心情去西政攻讀碩士學(xué)位,并且進(jìn)入張永和教授、梅傳強(qiáng)教授門下讀碩士,這和俞老師以及西政精神的感召、引領(lǐng)有很大關(guān)系。
在西政,我有幸通過(guò)俞門同學(xué)的引薦,踏入俞老師給博士生開設(shè)的法律思想史課堂,完整地旁聽(tīng)了他一學(xué)期的課程。俞老師研究孔子,也實(shí)踐孔子的教學(xué)方法。他的授課主要是討論啟發(fā)式的:學(xué)生暢所欲言,他一一提示、評(píng)點(diǎn),回答學(xué)生提問(wèn)。有一次他還把課堂搬到南山植物園,帶學(xué)生一起在植物園里品茗讀書。在教學(xué)上,他十分重視原典的研讀,強(qiáng)調(diào)宏觀把握與微觀考證相結(jié)合,主張讀史應(yīng)史論兼顧、考史品人、酌古斟今。
永遠(yuǎn)“在崗”的學(xué)者
以前通過(guò)閱讀著作只能了解到平面化的俞老師。在課堂和課下交流中,我則觀察和體悟到這位睿智長(zhǎng)者所傳承的文化之“道”。
我見(jiàn)到俞老師的時(shí)候,他已從社科院任上退休,擔(dān)任重慶市人大法制委員會(huì)主任委員和市人大常委會(huì)駐會(huì)委員。聽(tīng)先生說(shuō),他自己意愿本是想到政協(xié)任職(他曾任全國(guó)政協(xié)委員),因?yàn)檎f(xié)不用坐班,可以全心投入學(xué)術(shù)研究和教書育人。但是,組織上最終把他放在人大法制委的重要崗位。作為一個(gè)在哪里都會(huì)發(fā)光的領(lǐng)導(dǎo)干部,俞老師服從安排,兢兢業(yè)業(yè)的工作五年,為重慶地方立法盡了一個(gè)老法學(xué)家的微薄之力。
由于立法工作非常繁雜,他的精力被分割為兩部分:工作時(shí)間主要是在人大,業(yè)余時(shí)間在西政帶博士。所以,他在完成兩份工作(但領(lǐng)一份工資)的同時(shí),精力所限,只好放棄部分學(xué)術(shù)上的既有規(guī)劃。在《道統(tǒng)與法統(tǒng)》中,他提到自己座右銘的改變:六十歲以前“盡人事而知天命”,是為“人能弘道,道法自然”;六十歲以后,“學(xué)會(huì)放棄,完善自我”。我想就是這個(gè)客觀原因造成的。
但是,我理解俞老師所謂的“學(xué)會(huì)放棄”,是他實(shí)際用極高的標(biāo)準(zhǔn)要求自己。其實(shí),十年來(lái)在傳承古今中西法文化方面,他從來(lái)沒(méi)有放棄作為一名著名學(xué)者的責(zé)任感和使命感。
就我閱讀所及,近十年俞老師的論著,不僅成果豐碩,而且質(zhì)量上乘。我粗略統(tǒng)計(jì),他十年間僅就達(dá)到近百篇。出版三部獨(dú)著:《文化與法文化》《從儒家之法出發(fā)――俞榮根講演錄》《應(yīng)天理 順人情――儒家法文化》。他還主編或合著三部專著:《地方立法后評(píng)估研究》《中國(guó)傳統(tǒng)法學(xué)述論――基于國(guó)學(xué)視角》《尋求法的傳統(tǒng)》,并且主編《天憲》《法鑒》等學(xué)術(shù)集刊。
俞老師在關(guān)于中華法系、中國(guó)法律思想史、法制史、法文化、法律國(guó)學(xué)、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法律古籍文獻(xiàn)整理等均有獨(dú)創(chuàng)性的貢獻(xiàn)。他的論著由于立意深遠(yuǎn),高屋建瓴,視域縱橫中外,既重視理論建構(gòu)和經(jīng)典思想的發(fā)微,也重視考據(jù)和微觀實(shí)證,具有很強(qiáng)的說(shuō)服力和影響力。難能可貴的是,作為老一輩學(xué)者,他重視總結(jié)和反思,特別是對(duì)自己早年一些觀點(diǎn)的論點(diǎn)提法進(jìn)行更新,論據(jù)進(jìn)行補(bǔ)充。例如,對(duì)于古代法是否有確定性的問(wèn)題,他就三次修改自己的論文,最終提出罪刑法定和罪刑非法定和合這個(gè)觀點(diǎn)。近年來(lái),俞老師強(qiáng)調(diào)要尋找中國(guó)古代法的“自我”,對(duì)禮法問(wèn)題應(yīng)深入研究,應(yīng)當(dāng)擯棄對(duì)傳統(tǒng)法“古而有之”和“萬(wàn)事不如人”兩種錯(cuò)誤的認(rèn)識(shí)思維。針對(duì)論文選題碎片化和邊緣化的問(wèn)題,他呼吁中青年學(xué)者要集中研究中華法系主干線上的關(guān)鍵問(wèn)題(他形象稱為“進(jìn)入主干,逐鹿中原”)。這些觀點(diǎn)都頗有見(jiàn)地,得到了學(xué)界共鳴。
俞榮根教授不僅繼續(xù)深化、總結(jié)自己儒家法文化的研究,近十年來(lái)他還結(jié)合自己本職工作還開創(chuàng)了一些新的研究領(lǐng)域。例如,因?yàn)樗诘胤搅⒎ê腿舜笾贫鹊睦碚摵蛯?shí)踐方面的真情投入,所以在立法后評(píng)估、立法聽(tīng)證、立法助理、地方人大制度建設(shè)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不少心得和成果,為地方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展特別是地方立法提供了大量有價(jià)值的意見(jiàn)建議。
最近,在俞老師的七十壽宴上,蔣海松博士(現(xiàn)為湖南大學(xué)教師)用俞老師多本著作名稱連綴而成一首壽聯(lián),表達(dá)對(duì)其著作等身的敬仰。上聯(lián)側(cè)重介紹他在“立言”方面的貢獻(xiàn):“從儒家之法出發(fā),艱難開拓,論孔子,成通論,修大典,傳道統(tǒng),國(guó)學(xué)通覽,增彩四千年中華法苑。”(融入《從儒家之法出發(fā)》《艱難的開拓――的法思想與法實(shí)踐》《論孔子》《儒家法思想通論》《中華大典》《道統(tǒng)與法統(tǒng)》《國(guó)學(xué)通覽》《中華法苑四千年》等書)下聯(lián)側(cè)重他在“立功”方面的貢獻(xiàn):“向傳統(tǒng)之法尋求,耕耘不輟,秉天憲,評(píng)立法,譜渝史,播文化,儒言治世,無(wú)悔七十載壯麗人生!”(融入《尋求法的傳統(tǒng)》《天憲》《地方人大立法后評(píng)估制度研究》《當(dāng)代重慶簡(jiǎn)史》《文化與法文化》《儒言治世――儒學(xué)的治國(guó)之術(shù)》等書及俞老師的筆名“耘耕”)
俞老師卓越的學(xué)術(shù)成就和敏銳把握與深刻洞察學(xué)界動(dòng)態(tài),和他對(duì)事業(yè)的熱愛(ài)與勤奮是分不開的。在2010年主持校訂《中華大典》時(shí),他親自帶頭晚上加班到深夜。在治學(xué)方面,他為學(xué)生和中青年學(xué)者做出了表率。
傳承儒者為學(xué)為人之“道”
重視傳承,反映到俞老師與老一輩學(xué)者、友人的交往、情誼上。他通過(guò)身體力行、言傳身教,告訴學(xué)生們?nèi)绾螌?duì)待老師、如何與學(xué)界朋友交往。誠(chéng)如北航趙明教授所說(shuō),孔子和儒家法文化傳統(tǒng),在先生多年精湛的研究中,已經(jīng)潛入他的心靈深處,轉(zhuǎn)化為精神血脈。他的言行讓年輕人不同程度地領(lǐng)會(huì)到了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仁愛(ài),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忠孝。他除了為楊景凡教授編訂《景凡文存》,在張警教授八十壽誕時(shí),他還主持整理出版張先生多年未能出版的《〈晉刑法志〉注》手稿。林向榮教授去世時(shí),俞老師以《西政君子》一文,記錄下一個(gè)真正學(xué)人和教育家的偉大人格形象,通過(guò)林先生的人格形象以載“道”、以傳“道”。臺(tái)灣黃靜嘉教授、南京大學(xué)錢大群等同道出版新著,他擠出時(shí)間撰寫書評(píng)予以推介。
俞老師重視傳承,還反映到他對(duì)學(xué)生的熱愛(ài),講臺(tái)的鐘情上。《從儒家之法出發(fā)――俞榮根講演錄》記錄了俞老師近年來(lái)在西政乃至全國(guó)各種講壇上的風(fēng)采。校園刊物《法論》向俞老師約稿,他專門寫了長(zhǎng)篇回憶錄《一個(gè)老研的回憶》,詳細(xì)記敘西政最早一屆研究生學(xué)習(xí)的點(diǎn)滴往事。蔣海松博士讀研期間經(jīng)常組織的研究生學(xué)術(shù)活動(dòng),有時(shí)邀請(qǐng)俞老師參加,先生總是慨而應(yīng)允。
在有些高校,從學(xué)科建設(shè)角度,一些有學(xué)統(tǒng)傳承的學(xué)科就比較團(tuán)結(jié),發(fā)展較好。學(xué)統(tǒng)之傳,一是要有人“帶”。老輩給小輩創(chuàng)造脫穎而出的機(jī)會(huì),并提攜幫助。這里關(guān)鍵是老輩水平和境界要高。水平高,就不怕年輕人超越自己,境界高,就能樂(lè)見(jiàn)自己被小輩超越,而且在核心利益上出手幫助小輩。二是要有人“傳”,小輩以老輩衣缽傳人、發(fā)揚(yáng)老輩學(xué)說(shuō)為己任。這里的關(guān)鍵是小輩要有能力,而且人品正。老輩帶,小輩傳,各具其位,各守其責(zé),一個(gè)學(xué)派才能形成并興旺。作為學(xué)生,俞老師是西政楊景凡等老一輩學(xué)者的優(yōu)秀傳人;作為老師,他則是很多中青年學(xué)者的引路人和出色導(dǎo)師。
篇(2)
理論思想的改革與禮儀活動(dòng)的實(shí)踐畢竟還不是一回事,而正像《唐六典》撰作并非為了重定制度一樣,以“改撰”或者“折衷”出發(fā)的《開元禮》也并不與禮儀的再建直接掛鉤。但是,這不等于在禮書的撰作之先完全沒(méi)有準(zhǔn)備。恰恰相反,在《開元禮》撰作以前,唐朝廷從設(shè)立禮儀使開始,便相機(jī)進(jìn)行了大規(guī)模、高規(guī)格的立廟、祭天地和封禪等活動(dòng),這些禮儀活動(dòng)與經(jīng)濟(jì)形勢(shì)的變化緊密相連,在開元十至十四年分為兩個(gè)單元進(jìn)行,從而為《開元禮》的撰作進(jìn)行了最基礎(chǔ)、最實(shí)際的禮儀整備。
(一)禮儀使的設(shè)立和開元十年后的祭祖郊天
上面已經(jīng)說(shuō)明,在《開元禮》撰作之前,開元十年已有禮儀使的設(shè)立。禮儀使的設(shè)立,在相當(dāng)成分上與以往禮制中的矛盾有關(guān)。但矛盾的解決,以及儀注的撰作,實(shí)基于日常禮儀活動(dòng)和朝廷典禮的應(yīng)用。由開元中禮儀使的設(shè)立來(lái)看,其最直接的目的還在于開元中構(gòu)建盛世、更張禮儀的需要。可以說(shuō)明這一點(diǎn)的就是此后一系列郊廟祭祀的舉辦。這其中極為重大的一項(xiàng)就是開元十一年的南郊大典。《舊唐書》卷八《玄宗》上:
(開元十一年)十一月戊寅,親祀南郊,大赦天下,見(jiàn)禁囚徒死罪至徒流已下免除之。升壇行事及供奉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jí),四品轉(zhuǎn)一階。武德以來(lái)實(shí)封功臣、知政宰輔淪屈者,所司具以狀聞。賜酺三日,京城五日。
與唐朝大多數(shù)皇帝不同,玄宗即位以后只有祭祖而未舉辦過(guò)郊天的活動(dòng),開元十一年的南郊親祀是第一次,為此并舉行了大赦和大酺。大典由宰相親自主持。同書卷二一《禮儀》一在玄宗親享圓丘之下,記“時(shí)中書令張說(shuō)為禮儀使,衛(wèi)尉少卿韋為副,說(shuō)建議請(qǐng)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這里張說(shuō)所任禮儀使即宰相遇有大祀或國(guó)恤時(shí)的臨時(shí)任使,頗相當(dāng)于后來(lái)的大禮使。值得注意的是韋作為副使和實(shí)際組織者參加了這項(xiàng)活動(dòng),說(shuō)明禮儀使的設(shè)立與以上活動(dòng)有關(guān)。而大典的進(jìn)行看來(lái)也并不是突然進(jìn)行而先期無(wú)所準(zhǔn)備。《唐大詔令集》卷六八《開元十一年南郊赦》在刻意渲染了升平氣象之后稱:“所以今年獻(xiàn)春,恭祀后土;季秋吉日,追崇九廟;采先典于魯經(jīng),積肆類于虞典。”說(shuō)明在南郊之前,已先有祀后土與祭九廟的活動(dòng)。
唐朝的宗廟制度在玄宗以前,神主以七廟為限。故玄宗即位后,以睿宗升祔,即不得不將中宗遷至別廟。至開元五年正月,玄宗將行幸東都,以太廟屋壞,乃奉七廟神主于太極殿,玄宗親謁而發(fā)。開元六年玄宗還京,廟成,行親祔之禮。時(shí)已有河南人孫平子提出中宗不應(yīng)遷于別廟的問(wèn)題,因太常博士蘇獻(xiàn)“固執(zhí)前議”而得到宰相蘇颋支持,“平子之議竟不得行。”(37) 但是至開元十年,廟制終有變革。《通典》卷四七《天子宗廟》:
(開元)十年,制移中宗神主就正廟,仍創(chuàng)立九室。其后制獻(xiàn)祖、懿祖、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太廟九室也”。
建立九室事《舊唐書》卷二五《禮儀》五記在開元十一年春,時(shí)玄宗自洛陽(yáng)還京師,下制崇建宗廟,“于是追尊宣皇帝為獻(xiàn)祖,復(fù)列于正室,光皇帝為懿祖,并還中宗神主于太廟。及將親祔,會(huì)雨而止,乃令所司行事。”玄宗雖因故未能親參祔祭,但這一改宗廟神主七室為九室的舉措,已經(jīng)是對(duì)以往宗廟制度的巨大變革。而幾乎與此同時(shí),又有專為祈谷的汾陰后土之祀。《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四載:
汾陰后土之祀,自漢武帝后廢而不行。玄宗開元十年,將自東都北巡,幸太原,便還京,乃下制曰:“王者承事天地以為主,郊享泰尊以通神。蓋燔柴泰壇,定天位也;瘞埋泰折,就陰位也。將以昭報(bào)靈祗,克崇嚴(yán)配。爰逮秦、漢,稽諸祀典,立甘泉于雍峙,定后土于汾陰,遺廟嶷然,靈光可燭。朕觀風(fēng)唐、晉,望秩山川,肅恭明神,因致禋敬,將欲為人求福,以輔升平。今此神符,應(yīng)于嘉德。行幸至汾陰,宜以來(lái)年二月十六日祠后土,所司準(zhǔn)式。”
汾陰后土之祀始于漢武帝。據(jù)說(shuō)由于武則天時(shí)曾移梁山神于祠,使有司設(shè)壇祭祀如皇地祗而獲寶鼎,故“(開元)十一年二月,上親祠于壇上,亦如方丘儀。禮畢,詔改汾陰為寶鼎。亞獻(xiàn)邠王守禮、終獻(xiàn)寧王憲已下,頒賜各有差”。九廟建成后,祭祖先和祭后土都是重要祀事,所謂“崇德配地,盡孝配親,存乎禮經(jīng),不可缺也”(38)。祀事自開元十年已有準(zhǔn)備,而分別于開元十一年春、秋二季舉行,在此之后,就是上述同年冬至的南郊告天之儀。“蓋春秋之大事,莫先乎祀;王者之盛禮,莫重于郊”(39),祭天的活動(dòng)在建九廟、祭土地后最終進(jìn)行,三者遂組成一個(gè)重大的禮儀單元。
那么,如此重大,有步驟、有計(jì)劃的禮儀活動(dòng)為什么會(huì)在開元十年以后相繼進(jìn)行?對(duì)此金子修一先生已有說(shuō)明,指出是隨著國(guó)內(nèi)形勢(shì)的好轉(zhuǎn)、祥瑞的出現(xiàn)和外族來(lái)訪繼至而實(shí)現(xiàn)的。(40) 但是,若注意到同期朝廷的其他重大舉措,會(huì)發(fā)現(xiàn)玄宗剛好在任命禮儀使同時(shí)命宇文融任使括田括戶,以解決朝廷的財(cái)政危機(jī)。禮儀活動(dòng)和括田括戶,就性質(zhì)而言,一為禮儀文化也即意識(shí)形態(tài),一為戶口財(cái)政也即經(jīng)濟(jì)建設(shè),實(shí)涵蓋了現(xiàn)代意義上精神、物質(zhì)兩方面的追求。開元十年是玄宗即位殆將一紀(jì),經(jīng)過(guò)最初幾年的全力調(diào)整之后進(jìn)入了統(tǒng)治承平期。只是這時(shí)的社會(huì)還遠(yuǎn)遠(yuǎn)沒(méi)有達(dá)到富裕,所以這個(gè)時(shí)期的玄宗,一方面致力于改善經(jīng)濟(jì),強(qiáng)調(diào)“固茲邦本,致諸升平”及“有國(guó)者必以人為本,固本必以食為天”的“勸農(nóng)之道”,承認(rèn)武則天以來(lái)由于對(duì)西北用兵及遇兇年造成“水旱相仍,逋亡滋甚”的局面,允許逃戶自首,要求宇文融“巡按郡邑,安撫戶口”,對(duì)于“賦役差科,于人非便者,并量事處分”(41);另一方面,即開始通過(guò)禮儀活動(dòng)完善國(guó)家禮法,樹立朝廷形象,突出皇帝權(quán)威。這一點(diǎn)說(shuō)明玄宗是以典型的古帝王統(tǒng)治術(shù)與理想境界作為追求。所謂《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孔穎達(dá)以為,“足衣食祭鬼神,必當(dāng)有所安居”(42)。因此“食貨”與“祀”乃不可分割的兩部分。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使民衣食足用的同時(shí),必須以敬祀鬼神作為精神象征,因此玄宗的“盛世”理想應(yīng)該是包含這兩個(gè)方面的。
有跡象表明這個(gè)時(shí)期的經(jīng)濟(jì)整頓已經(jīng)是初見(jiàn)成效。《唐大詔令集》卷六七《開元十一年郊天制》稱:“今四夷內(nèi)附,諸侯率職,群生和洽,萬(wàn)物阜蕃。”而前揭《南郊赦》也有所謂宗廟降靈,乾坤交泰,遠(yuǎn)人來(lái)歸的渲染。與此相應(yīng),上述完善宗廟的建置和對(duì)于祖、天、地三者的祭祀在這一時(shí)期進(jìn)行,也可以說(shuō)是為實(shí)現(xiàn)《開元禮》制的再建打下了根基。
首先是祖廟問(wèn)題,上面已經(jīng)說(shuō)明,玄宗開元十至十一年下制增宗廟七室為九室是這一階段內(nèi)對(duì)禮儀的第一個(gè)大變革。“七廟”之說(shuō)見(jiàn)于《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以為從周代開始實(shí)行七廟制度,由太祖(后稷)加上文王武王再加上四親廟(高、曾、祖、父)組成。但是王肅不同意這樣的說(shuō)法,認(rèn)為文王、武王應(yīng)在七廟之外,為不遷之主。或認(rèn)為,唐玄宗所改九室之制是從王肅之說(shuō)。(43) 但是玄宗開元十年制只以“禮從時(shí)變”、“因宜創(chuàng)制”的說(shuō)法來(lái)標(biāo)榜創(chuàng)新,增加懿、獻(xiàn)二祖和使中宗入廟也是以“孝思”為名,并不是像王肅那樣,是從“殊功異德”來(lái)解釋宗廟的“不遷”,可見(jiàn)玄宗的改禮也并非僅僅追隨王肅,而是有自己的問(wèn)題要解決。在此之前,隨著已死皇帝數(shù)量的增加和兄弟相繼等特殊原因,圍繞宗廟神主的遷祔不斷引起爭(zhēng)論,七廟制度不足以解決這樣的矛盾。而玄宗增加廟室,不僅可以顯示孝悌之道,顯示不斷延續(xù)的大朝風(fēng)范,也擴(kuò)大了宗廟本身的建置,為未來(lái)更加復(fù)雜的遷祔問(wèn)題預(yù)留了余地。所以,雖然后來(lái)宗廟還有變化,但九廟制度(最多時(shí)為九廟十一室),卻成為唐朝皇帝遵守的“不遷之典”。
其次是郊天。開元十一年十一月的郊天是玄宗朝皇帝親郊的第一次實(shí)踐。冬至祭昊天上帝雖然《貞觀禮》已定,但一方面,史載此次郊天使張說(shuō)重定郊禮圖,“詔遂頒于有司,以為常式”(44),事實(shí)上是依據(jù)《顯慶禮》而進(jìn)一步確定了昊天的獨(dú)尊,另一方面,郊天的配享是此次最重大的改革。唐初本來(lái)是按照郊祀的不同對(duì)象實(shí)行分別配享。如武德初定景帝、元帝分配天地,貞觀詔改高祖與景帝、元帝。高宗增加太宗取消元帝,乾封中又下令圓丘、明堂、感帝乃至方丘皆以高祖、太宗并配。至垂拱元年,武則天接受了鳳閣舍人元萬(wàn)頃、范履冰等建議,始在郊天地中行高祖、太宗、高宗三祖同配之禮。(45) 由張說(shuō)建圓丘以高祖單獨(dú)配天而終于改變。
以高祖單獨(dú)配天涉及到是否以太祖為尊的問(wèn)題,對(duì)于《禮記》所說(shuō)的太祖,鄭玄解釋為始封之祖。張說(shuō)的建議卻第一次確立了高祖在宗廟中的獨(dú)尊地位。這一決定顯然與《顯慶禮》定昊天獨(dú)尊有關(guān),由于天的惟一性對(duì)應(yīng)著人神的惟一性,所以用以配天的宗廟祖宗中的獨(dú)尊之位也需要隨之確立,并且從尊位選擇建功立業(yè)的開國(guó)之君高祖而不是始封之主的太祖來(lái)看,也是繼承了貞觀、顯慶兩禮主要以高祖祭天,突出唐朝的建立和國(guó)家權(quán)威的一貫。這是《開元禮》繼承并發(fā)展兩禮改革的一例。此后《開元禮》即定以高祖配圓丘、祈谷、方丘,以太宗配雩祀、神州,以睿宗配明堂。但是直至代宗寶應(yīng)元年歸崇敬等建議以太祖為始封之主配天以前,高祖的地位始終沒(méi)有變。從后來(lái)黎幹進(jìn)狀批駁以太祖配天多指鄭玄之誤看,以太祖配天確實(shí)主要有鄭玄理論作依據(jù)(46),所以玄宗定高祖獨(dú)尊以配天的同時(shí),就不獨(dú)是針對(duì)鄭玄,也打破了《禮記》以太祖作為始封之主的權(quán)威。
第三是后土。后土是所謂“崇德配地”,應(yīng)與天帝相對(duì)。但與前兩者屬于傳統(tǒng)儒家祭祀不同,儒家的土地在唐禮另有皇地祗,而汾陰后土之祭,由《史記·封禪書》的記載卻知道是始自漢武帝而與黃帝獲神鼎見(jiàn)太一的神仙傳說(shuō)聯(lián)系在一起。所以,雖然玄宗在返京的途中親祭后土,說(shuō)是“為蒼生祈谷”(47),真正意義卻是為天子禱福,是玄宗一系列神仙祭的開始。對(duì)于后來(lái)封禪與其他道教神仙祭祀而言,后土祭僅僅是鋪墊,但《開元禮》卷二九“皇帝夏至祭于方丘”之下,卻注明“后土禮同”,說(shuō)明在《開元禮》中,是給后土與皇地祗同等的地位,可見(jiàn)玄宗在對(duì)“地”的祭祀中也開了新的篇章。
擴(kuò)建祖廟,郊天和后土,玄宗都解決了一些難題,并有不同于前人或前禮的新創(chuàng)建,但這只是開始,更重要的禮儀實(shí)踐還有待封禪大典的完成。
(二)封禪大典的告成之儀
在郊天的活動(dòng)舉行經(jīng)過(guò)一段時(shí)間之后,開元十三年玄宗終于舉辦了封禪大典。封禪是帝王有大德有大功才可以進(jìn)行的隆重祀事。《開元十三年封泰山詔》稱。“自古受命而王者,曷嘗不封泰山,禪梁父,答厚德,告成功,三代之前,罔不由此”(48),便證明了這一點(diǎn)。開元十三年為什么可以“告成”呢?雖然張說(shuō)歌頌玄宗“創(chuàng)九廟,禮三郊,大舜之孝敬也;敦九族,友弟兄,文王之慈惠也;卑宮室,菲飲食,夏禹之恭儉也;道稽古,德日新,帝堯之文思也;憐黔首,惠蒼生,成湯之深仁也;化玄漠,風(fēng)太和,軒皇之至理也”(49),似乎功蓋堯舜禹湯,但這里最實(shí)在的一個(gè)成績(jī),其實(shí)是上面所說(shuō)的宇文融括戶。眾所周知,宇文融括戶在相當(dāng)大的程度上解決了財(cái)政困境,促進(jìn)了物資流通。《通典》卷七《歷代盛衰戶口》在記述他事跡的文字之下便說(shuō)道:
至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無(wú)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二文。東至宋汴,西至歧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奉溢。每店皆有驢貨客乘,倏忽數(shù)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yáng),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yuǎn)適數(shù)千里,不持寸刃。
史家夸贊開元盛世莫不以此為根據(jù),因此封禪正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取得極大成效的同時(shí)舉辦的精神慶典。史載此次封禪同樣由張說(shuō)、韋加以組織并由康子元等定封禪儀。參加儀式有文武百僚、二王后、孔子后、諸方朝集使和“戎狄夷蠻羌胡朝獻(xiàn)之國(guó)”的首領(lǐng)與少數(shù)民族酋長(zhǎng),玄宗制稱“百神群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lái)慶,斯是天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并作《紀(jì)太山銘》,“御書勒于山頂石壁之上”,昭示天下,流傳后世,真可謂是“禮備封禪,功齊舜禹”了。(50)
封禪成功后,開元十四年正月,玄宗又令朝臣分祭五岳四瀆和風(fēng)伯雨師。《唐大詔令集》卷七四《命盧從愿等祭岳瀆敕》說(shuō)明:“五岳視三公之位,四瀆當(dāng)諸侯之秩,載于祀典,抑惟國(guó)章。方屬農(nóng)功,頗增旱暵。虔誠(chéng)徒積,神道未孚,用申靡愛(ài)之勤,冀能通潤(rùn)之感……且潤(rùn)萬(wàn)物者,莫先乎雨;動(dòng)萬(wàn)物者,莫疾乎風(fēng),睠彼靈神,允稱師伯。雖有常祀,今更陳請(qǐng)……各就壇場(chǎng),務(wù)加誠(chéng)敬,但修萍藻,不假牲牢,應(yīng)緣奠祭,允宜精潔。”其中雖強(qiáng)調(diào)了防水旱,但對(duì)象如此完全,不難理解其用心的周到。五岳四瀆和風(fēng)伯雨師是地位稍低于天地日月的神祗,因此封禪大禮與這類祭祀相和,在祭祖郊天之后就幾乎包括了對(duì)自然界所有重要神靈的享獻(xiàn),從而完成了玄宗展示盛世、溝通一切天神地祗的第二個(gè)禮儀單元。
封禪在玄宗以前,既有貞觀所定儀注,也有高宗和武后時(shí)期的成例可參,開元十三年封禪形制即多遵高宗。但是在玄宗下制令張說(shuō)、徐堅(jiān)等與禮官撰東封儀注后,張說(shuō)提出高宗乾封中禪社首山以“文德皇后配皇地祗、天后為亞獻(xiàn),越國(guó)太妃為終獻(xiàn)”,是“以宮闈接神,有乖授命易姓之事”,非古之制,并認(rèn)為中宗有大難也是因祀圓丘以韋后為亞獻(xiàn),因此奏請(qǐng)以睿宗配皇地祗。所以封禪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封臺(tái)之前壇”,以“高祖神堯皇帝配享”,同時(shí)享皇地祗于社首之泰折壇,也以“睿宗大圣真皇帝配祀”(51),改變了乾封中的二帝同配和皇后配享。這一改革也被吸收入后來(lái)的《開元禮》中。不僅如此,從史料所記封禪典禮看,開元十三年與前之重要不同,還在于改變了祭祀的程序和地點(diǎn)。《通典》卷五四《封禪》載其年十一月己丑,玄宗在侍從陪同下“御馬而登”。由于“帝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欲初獻(xiàn)于山上壇行事,亞獻(xiàn)、終獻(xiàn)于山下壇行事”,結(jié)果因賀知章奏昊天上帝和五方上帝,各自代表君臣之位,應(yīng)分別祭祀,“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誠(chéng)足以垂范來(lái)葉,為變禮之大者也”,所以將昊天壇由山下搬至山上,初、亞、終三獻(xiàn)一道進(jìn)行,五方帝及諸神座于山下壇行事。但山上只有皇帝和二、三大臣,與山下群臣分別,不僅簡(jiǎn)化了手續(xù),而且突出了昊天上帝及與之對(duì)應(yīng)的皇帝的獨(dú)尊。
封禪儀式對(duì)于玄宗的意義,還在于啟迪了他的修道成仙之心。由于自秦始皇和漢武帝已將封禪與神仙說(shuō)聯(lián)系起來(lái),后世則更在封禪中發(fā)展道教儀式,這一點(diǎn)在高宗武則天已是如此(52)。玄宗之所以接受道學(xué)之士賀知章建議,也是為了在封禪時(shí)實(shí)踐皇帝受“太一神策”,與神仙相接這一套自漢武帝即開始的儀式。而玄宗在理論方面也接受了康子元等人的建議。《新唐書》卷二《康子元傳》稱:
康子元,越州會(huì)稽人。仕歷獻(xiàn)陵令。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shuō)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xué)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陽(yáng)敬會(huì)真于說(shuō),說(shuō)藉以聞,并賜衣幣,得侍讀。子元擢累秘書少監(jiān),會(huì)真四門博士,俄皆兼集賢侍講學(xué)士。
玄宗將東之太山,說(shuō)引子元、行果、徐堅(jiān)、韋縚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說(shuō)、堅(jiān)、子元白奏:“《周官》:樂(lè)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lè),非緣燔也。宋、齊以來(lái)皆先嚌福酒,乃燎,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趙東曦儀議,以為:“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儀已而燔,神無(wú)由降。”子元議挺不徙。說(shuō)曰:“康子獨(dú)出蒙輪,以當(dāng)一隊(duì)耶?”議未判,說(shuō)請(qǐng)決于帝,帝詔后燔。
康子元也是專治易學(xué)和老莊的道學(xué)之士。“燔柴”是祭天中燔燒祭品的儀式,許敬宗提出先燔的理由是“周人尚臭”,遭到康、張等的辯駁。雖以《周官》為證,但問(wèn)題其實(shí)在儒家的血祭、葷祭與道教祭祀明顯不合,因此康、張的主張并非是儒學(xué)的論爭(zhēng),而是要改變和隱去“尚臭”的儒家觀念。“后燔”之說(shuō)后來(lái)也被貫徹于《大唐開元禮》的所有郊祀之中。因此,反映在《開元禮》雖然是對(duì)《貞觀禮》的采納,卻融入了道教意識(shí)。此后,玄宗更通過(guò)對(duì)遍及全國(guó)的川岳海瀆實(shí)行道教方式祭祀擴(kuò)大了影響,并于開元十六年以后逐步建立與道教有關(guān)的祠龍池等祀,限于本文篇幅不能細(xì)論,但是從封禪以后國(guó)家祭祀中出現(xiàn)的道教化傾向卻是無(wú)可置疑的。這表明皇帝的意志在禮儀的建設(shè)中愈來(lái)愈有決定的作用。
以上禮儀活動(dòng)的舉行都是為了使帝王展示自身功德和國(guó)家強(qiáng)盛,不過(guò)有著充分物質(zhì)和精神準(zhǔn)備的兩個(gè)禮儀單元的完成仍只是玄宗經(jīng)營(yíng)盛世的一部分。由于國(guó)家祭祀是五禮吉禮的核心,開元十至十四年兩個(gè)階段的皇帝郊廟祭祀,毋庸說(shuō)是進(jìn)行了最重要的禮儀實(shí)踐。宗廟祖宗和天地,是國(guó)家祭祀最基本、最重要的對(duì)象,封禪則是至高無(wú)上的皇帝典禮。而無(wú)論是哪一種儀注都越出了古禮的規(guī)定,可以說(shuō)玄宗對(duì)于“改撰”《禮記》已進(jìn)行了預(yù)演,“改撰”也不再是停留在學(xué)術(shù)討論的層面。而玄宗通過(guò)實(shí)踐無(wú)疑開始有了自己的理論和構(gòu)想,也完全有了改建禮儀的基礎(chǔ)和把握,這一點(diǎn)在舉行封禪儀式之后當(dāng)然就更是如此。無(wú)論祭祖、郊天和封禪活動(dòng)中,都不但有對(duì)前禮的選擇和辨證,也有一些完全不同已往的新儀注,增加了許多貞觀、《顯慶禮》不具有的新因素。總之,無(wú)論如何,以上內(nèi)容都表明唐朝開元的禮制比之貞觀、《顯慶禮》更加成熟而有獨(dú)創(chuàng)性,而禮儀的實(shí)踐或許也會(huì)進(jìn)一步刺激玄宗君臣為自己樹碑立傳、標(biāo)榜盛世的決心。所以當(dāng)著這些活動(dòng)完成的同時(shí),可以代表盛世精神象征的唐代“禮記”——《大唐開元禮》也就有了當(dāng)然的創(chuàng)作基礎(chǔ)。事實(shí)上《開元禮》確有對(duì)上述新典禮儀注的吸收,而如果將這個(gè)禮儀準(zhǔn)備過(guò)程算在內(nèi),則《開元禮》的醞釀應(yīng)與《唐六典》大致同時(shí),是從開元十年禮儀使的設(shè)立就開始了,禮儀使的設(shè)立因此也可以說(shuō)是構(gòu)建《開元禮》的最早標(biāo)志。
轉(zhuǎn)貼于
四、“改撰”與“折衷”的調(diào)和——《開元禮》的最后取舍
唐人曾經(jīng)指出,“《開元禮》,其源太宗創(chuàng)之,高宗述之,玄宗纂之曰《開元禮》”(53)。《開元禮》公認(rèn)是吸收和“折衷”貞觀、《顯慶禮》內(nèi)容而成。但本文業(yè)已說(shuō)明,對(duì)于《開元禮》曾經(jīng)有“改撰”和“折衷”的兩種意見(jiàn)。“改撰”之旨代表著玄宗取法周天子,試圖用代表唐朝禮法的《開元禮》和《唐六典》作為盛世禮典的意圖,因而對(duì)于現(xiàn)有禮制加以“折衷”的具體做法與“改撰”古《禮記》思想之間其實(shí)并不是完全對(duì)立的。問(wèn)題只是在于,對(duì)貞觀、顯慶二禮中因禮學(xué)依據(jù)不同所產(chǎn)生的矛盾如何折衷?折衷之后的《開元禮》又如何體現(xiàn)“改撰”?這里,有必要談一下《開元禮》最后階段的創(chuàng)作。
前揭《舊唐書·禮儀志》說(shuō):“初令學(xué)士右散騎常侍徐堅(jiān)及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檢撰,歷年不就。說(shuō)卒后,蕭嵩代為集賢院學(xué)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給人的印象是,似乎《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是完全由王仲丘完成的。由于張說(shuō)卒官是在開元十八年十二月,因此蕭嵩真正接替張說(shuō)應(yīng)當(dāng)是開元十九年初以后的事。(54) 從這時(shí)到《開元禮》成書不過(guò)一年多,雖然迅速成書可能出于玄宗的催促,但王仲丘在這樣短的時(shí)間內(nèi),是否能獨(dú)自完成這樣的一部巨制是很令人懷疑的。且從今所見(jiàn)《開元禮》對(duì)上述開元十至十四年郊祀等禮儀改革內(nèi)容的吸收,特別是玄宗令張說(shuō)、徐堅(jiān)、康子元等參定封禪儀注的情況,我們知道至少并不完全是如此,另外還有很多內(nèi)容其實(shí)是直接抄撮《貞觀禮》和《顯慶禮》,所以對(duì)于其中的大部分,王仲丘以前的作者們已有撰作,或者已作了大量的前期準(zhǔn)備工作。
不過(guò),史料證明確實(shí)還遺留有一些重要的問(wèn)題是由蕭嵩和王仲丘決定的。例如史載張說(shuō)開元十一年曾對(duì)郊天禮諸星的配祀作了一些調(diào)整。據(jù)《冊(cè)府元龜》卷五八九《掌禮部·奏議》一七載他與賀知章奏議,稱按祠令規(guī)定壇中祀“五星已下內(nèi)官五十三座,中官一百六十座,外官一百四座,眾星三百六十座”,但“今奉墨敕授尊卑升降,又新加降等座總?cè)僖皇?八?)座,并眾星三百六十九座,凡六百八十七座”;但據(jù)今本(洪氏公善堂本)《開元禮》和《通典》卷一九《開元禮纂類四》有內(nèi)官55座,中官159座,外官105座,眾星360座。外官眾星合為465座。仍近似于《祠令》(應(yīng)為開元七年)(55),而與張說(shuō)所定有不同。除此外更多地是涉及一些有爭(zhēng)議的內(nèi)容,如祭天禮中冬至祀圓丘和祈谷、大雩、明堂都是郊天最重要的儀目。其中除冬至祀昊天上帝已因張說(shuō)作郊禮圖可不論外,其他三儀都有依從《貞觀禮》六天說(shuō)(即郊天主祭除昊天并有五方帝、五人帝等)、抑或《顯慶禮》獨(dú)奉昊天的問(wèn)題。《舊唐書》卷二一《禮儀志》記乾封初,高宗詔依舊祀感帝與神州。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曰:“顯慶新禮,廢感帝之祀,改為祈谷,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檢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敕依舊復(fù)祈谷為感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依新禮見(jiàn)配圓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祗,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禮。”而接下來(lái)證明“有乖古禮”,就是引《禮記·祭法》和鄭玄注、《三禮義宗》、《禮記·大傳》等為據(jù),說(shuō)明其不合禮經(jīng)與先儒所論。明堂、雩祀當(dāng)然也是如此。所以同志又記:
儀鳳二年(公元677年)七月,太常少卿韋萬(wàn)石奏曰:“明堂大享,準(zhǔn)古禮鄭玄義,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玄義祀五天帝,顯慶已來(lái)新修禮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元三年三月敕,五禮并依貞觀年禮為定。又奉去年敕,并依周禮行事。今用樂(lè)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古禮及《貞觀禮》,為復(fù)依見(jiàn)行之禮?”時(shí)高宗及宰臣并不能斷,依違久而不決。尋又詔尚書省及學(xué)者詳議,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事,兼用貞觀、顯慶二禮。
可見(jiàn)一直以來(lái)使朝廷在用禮方面猶疑不定的正是這些內(nèi)容。但是蕭嵩和王仲丘使之得到了解決。史稱蕭嵩“一門盡貴”,“恩顧莫比”,與玄宗且為兒女親家,“每啟事必順旨”(56),對(duì)于玄宗的要求應(yīng)當(dāng)十分理解。《資治通鑒》卷二一三開元二十年八月條記曰:
初,上命張說(shuō)與諸學(xué)士刊定五禮,說(shuō)薨,蕭嵩繼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請(qǐng)依明(顯,避諱改)慶禮,祈谷、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請(qǐng)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從之。
《通鑒》所記甚簡(jiǎn),但據(jù)《新唐書》卷二《王仲丘傳》,說(shuō)明祈谷、大雩、明堂三者本來(lái)在貞觀、《顯慶禮》祭祀的對(duì)象和依據(jù)都有不同,但王仲丘卻根據(jù)“有其舉之,莫可廢之”的原則,“欲合貞觀、顯慶二禮”。即一方面認(rèn)為《顯慶禮》獨(dú)祀昊天上帝比較“合于經(jīng)”而主要繼承《顯慶禮》,以昊天為主祭;另一方面則以《貞觀禮》曾祭五方帝,也以之為配祀,這樣與原來(lái)的冬至主祭昊天統(tǒng)一,就達(dá)到了所謂“二禮并行,六神咸祀”的效果。
祈谷、大雩、明堂此前沒(méi)有定奪,應(yīng)當(dāng)是史料所說(shuō)《開元禮》“歷年不就”的一個(gè)原因。王仲丘的做法是在突出昊天的原則下,能夠盡量調(diào)和貞觀、《顯慶禮》的不同,從而將二禮兼收并蓄,解決了一直以來(lái)的矛盾。此外《通典》卷八九《齊衰杖周》也說(shuō)到開元二十年“中書令蕭嵩與學(xué)士改修五禮,又議請(qǐng)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為定,遂為成典”,卷九二《嫂叔服》說(shuō)到“中書令蕭嵩奏依《貞觀禮》為定”。這證明,當(dāng)時(shí)兇禮中五服制度的問(wèn)題在張說(shuō)時(shí)期也沒(méi)有解決。而從《開元禮》內(nèi)容來(lái)看,蕭嵩不但接受貞觀后期和《顯慶禮》的全部改革內(nèi)容(包括曾祖服、舅甥服、嫂叔服等),也增加了《顯慶禮》沒(méi)有,由武則天所提出的父在為母服三年制。所以,應(yīng)當(dāng)說(shuō)王仲丘和蕭嵩才是最終實(shí)現(xiàn)張說(shuō)“折衷”原則的人。
那么,既然一樣是“折衷”,為什么這些問(wèn)題在張說(shuō)主持的時(shí)期竟定不下來(lái)呢?這一點(diǎn)最值得深思。嚴(yán)耕望先生分析《唐六典》曾指出,其書“蓋欲全部摹仿《周禮》,即不能牽就現(xiàn)行官制,欲牽就現(xiàn)行官制,即不能全部摹仿《周禮》,此兩原則絕對(duì)不能兼顧也。后來(lái)學(xué)士于莫可奈何中,乃毅然放棄全部《周禮》之原則,一以現(xiàn)行職員令之官制為綱領(lǐng),詳其組織”,《唐六典》是放棄《周禮》原則成就的。《開元禮》也同樣有必須放棄《禮記》原來(lái)篇目形式,而以唐五禮為綱,詳其內(nèi)容,詳其制度的問(wèn)題。
但筆者認(rèn)為,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開元禮》要改變《禮記》的許多內(nèi)容思想。問(wèn)題是張說(shuō)雖然與禮官撰東封儀注,并定高祖配天等有所改革;但既然認(rèn)為《禮記》是不刊之典,原則上就要奉之為準(zhǔn)繩為圭臬,不能動(dòng)輒“改撰”,這是張說(shuō)和王喦的分歧所在。因而其所主張的折衷,也是要從貞觀、《顯慶禮》中擇善而從。但他無(wú)法解決貞觀、《顯慶禮》明顯的矛盾,也無(wú)法完全不顧及古禮原則,不考慮學(xué)術(shù)正誤和前賢傳釋。遇到《禮記》或前儒說(shuō)中明顯有矛盾而與唐制沖突的問(wèn)題,就難免使學(xué)士們陷入困惑,無(wú)所決斷。特別如昊天獨(dú)祭與五帝合祭的不同主張影響到祈谷、大雩、明堂祭祀,更毋庸說(shuō)貞觀、顯慶以來(lái)的服制改革都與《儀禮》作為經(jīng)文、《禮記》作為儀注的原則相去太遠(yuǎn)。按照古禮經(jīng)文、儀注和前儒注疏,這些改革就不能接受。學(xué)者們?nèi)粼谶@些問(wèn)題上各執(zhí)己見(jiàn),莫衷一是,就必然會(huì)曠日持久,徒勞無(wú)功。而蕭嵩和王仲丘的“折衷”卻是以唐朝新制度為著眼點(diǎn),不強(qiáng)調(diào)禮經(jīng),不非議鄭王,不一味在學(xué)術(shù)上作糾纏。雖然《開元禮》是以繼承《顯慶禮》為主體,但對(duì)于無(wú)論是貞觀、顯慶還是這之后的改革,也無(wú)論是否合乎古禮或前儒之說(shuō),幾乎都以“有其舉之,莫可廢之”的態(tài)度心平靜氣地接受。當(dāng)《貞觀》、《顯慶禮》有矛盾時(shí),只是采取略加變通的辦法加以調(diào)和,用這樣的方法肯定唐朝自己的創(chuàng)造,這說(shuō)明他們?cè)趯?shí)際上已經(jīng)不唯古禮和先儒馬首是瞻,而是建立了新的取舍標(biāo)準(zhǔn)。惟其如此,他們的“折衷”才能不受牽制,更加徹底;惟其如此,才能實(shí)現(xiàn)《開元禮》對(duì)《禮記》從內(nèi)容到精神上的改撰。
總之,徹底的“折衷”其實(shí)就是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古禮原則、內(nèi)容上的“改撰”,而蕭嵩和王仲丘的作法也說(shuō)明,“折衷”本來(lái)就與變革分不開。不過(guò)對(duì)他們,已經(jīng)不能完全用“鄭王擇從”來(lái)涵蓋,也不能僅以學(xué)術(shù)取向去作解釋。這樣說(shuō)當(dāng)然并不是認(rèn)為《開元禮》毫無(wú)學(xué)術(shù)根底,沒(méi)有吸收漢魏南北朝禮學(xué)變化作為依據(jù),而是所謂“鄭王擇從”,充其量只是在貞觀、《顯慶禮》已經(jīng)“考取鄭王”的基礎(chǔ)上再加擇從,或者再加擴(kuò)大而已,并不是《開元禮》自身創(chuàng)建的惟一特色和依據(jù)。如前所述,唐初以后,唐人從疑注到改經(jīng)的傾向已經(jīng)愈來(lái)愈明顯,并且這種“改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常常已經(jīng)不是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的選擇而是配合著時(shí)代維新的需要,是對(duì)帝王意旨的認(rèn)同和屈從。玄宗的“詔可”就表明了皇帝在背后對(duì)他們的支持。既然蕭嵩被任命時(shí),已明確要建造唐朝的“不刊之典”,《開元禮》又是要體現(xiàn)唐朝特色,他們的選擇,就只能是直接針對(duì)唐禮和唐制(而不完全是前儒學(xué)說(shuō))已有內(nèi)容的選擇;他們的折衷,也只能是前后改革基礎(chǔ)上的折衷。事實(shí)上,蕭嵩主持期間,不僅確定了以上重大內(nèi)容,而且通過(guò)吸收開元二十年以前的格式制敕入禮,對(duì)于禮儀作了其他許多修改,對(duì)此,我們將在另文闡述。因此,所謂“網(wǎng)羅遺逸,芟翦奇邪”,是蕭嵩和王仲丘不同于張說(shuō)、徐堅(jiān)之處,也正是由于這一點(diǎn),《大唐開元禮》才可能最終成就于他們之手。而他們?cè)诮?gòu)唐朝新制,顯示盛世獨(dú)創(chuàng)精神的同時(shí),與其說(shuō)是繼承了張說(shuō)的“折衷”意圖,不如說(shuō)是實(shí)現(xiàn)了玄宗的“改撰”和取代之旨更符合實(shí)際。
昔人對(duì)《開元禮》有極高的評(píng)價(jià)。歐陽(yáng)修曾謂《開元禮》使“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后世用之,雖時(shí)小有損益,不能過(guò)也”(57)。《四庫(kù)全書總目提要》稱贊說(shuō):“其討論古今,斟酌損益,首末完備,粲然勒一代典制,誠(chéng)考禮者之圭臬—也。”近代學(xué)者章太炎也以為“擇善而從,宜取其稍完美者,則莫尚于《開元禮》矣”(58)。當(dāng)今研究者論述《開元禮》,更提出具有總結(jié)性、全面性、系統(tǒng)性的三大特點(diǎn)(59)。但是綜觀上述,筆者認(rèn)為《開元禮》不過(guò)是唐玄宗努力營(yíng)造大唐盛世,以新代舊、以“今”化古的產(chǎn)物。因此一方面,《開元禮》繼貞觀、《顯慶禮》之后,使唐前期五禮更加定型化,從而確立了中古禮制的框架,實(shí)現(xiàn)了國(guó)家強(qiáng)盛、經(jīng)濟(jì)繁榮之際的禮儀輝煌;但另一方面,《開元禮》吸收貞觀、《顯慶禮》和開元時(shí)代的變革成果,本身也必然充斥著許多離經(jīng)叛道的新內(nèi)容,表現(xiàn)了唐國(guó)家禮儀完全不同于上古禮的時(shí)代特色,這是《開元禮》所以“粲然勒一代典制”,成為時(shí)展進(jìn)步之里程碑的中心所在。雖然,就唐國(guó)家禮制而言,《開元禮》并不是變革的結(jié)束,但它肯定了南北朝和唐初以來(lái)的變化,突破了古禮經(jīng)的內(nèi)容與思想格局,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興官僚和士人的理想和追求,其創(chuàng)新精神,也必然為唐中后期的禮制改革奠定了基礎(chǔ)。中古時(shí)代的禮制就是按照《貞觀禮》《顯慶禮》《開元禮》開辟的途徑不斷變化,從而適應(yīng)時(shí)代需要,體現(xiàn)國(guó)家和皇帝權(quán)威,指導(dǎo)朝廷政治和社會(huì)生活。總之,作為上層建筑的禮,與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同步,它的產(chǎn)生既有著極強(qiáng)的目的性,也有著極為鮮明的現(xiàn)實(shí)性。這是《開元禮》所給予的啟示,而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還有待我們?cè)谖磥?lái)的研究中繼續(xù)予以證明。
附記:本文在歷史所學(xué)術(shù)沙龍報(bào)告后,得到不少同仁的批評(píng)指正,特別是樓勁先生在《開元禮》的學(xué)術(shù)背景等方面提出許多具體建議與幫助。特此說(shuō)明并致謝。
注釋:
①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八二《開元禮》,商務(wù)印書館1959年重印版,第892頁(yè)。
②見(jiàn)《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禮儀篇》,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61頁(yè)。
③《唐令拾遺》,東方文化學(xué)院東京研究所1933年版;《唐令拾遺補(bǔ)》,東京大學(xué)出版會(huì)1997年版。此前瀧川政次郎有《唐禮與日本令》,法學(xué)協(xié)會(huì)雜志,第47卷9期,1929年;此外1972年池田溫?fù)?dān)任解題的《大唐開元禮》一書刊行,也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④見(jiàn)池田溫編《中國(guó)禮法と日本律令制》并書中氏著《唐令と日本令——〈唐令拾遺補(bǔ)〉編纂にょせて——》一文,東方書店1992年版。并參池田溫《大唐開元禮〈附大唐郊寺錄〉》初版序言和二版附記。代表作又如渡邊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國(guó)古代帝國(guó)の朝政ヒ儀禮》,柏書房1996年版。金子修一《古代中國(guó)朝政ヒ皇帝祭祀》,汲古書院2000年版。此外專題論文又有西崗市佑《“大唐開元禮”“薦新于太廟”之儀》(《國(guó)學(xué)院中國(guó)學(xué)會(huì)報(bào)》40,1994年)和《“大唐開元禮”中之七祀》(《國(guó)學(xué)院雜志》97,1996年11月)等。
⑤如丘衍文《唐代開元禮中喪禮之研究》,臺(tái)北郁氏印書及獎(jiǎng)學(xué)基金會(huì)1984年版;張長(zhǎng)臺(tái)《唐代喪禮研究》;甘懷真《〈大唐開元禮〉中天神觀》,臺(tái)灣《第五屆唐代文化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論文集》,嘉義中正大學(xué)2001年版,第447—449頁(yè);高明士也有關(guān)于《開元禮》版本的研究,見(jiàn)氏著《戰(zhàn)后日本的中國(guó)史研究》(修訂版),臺(tái)北明文書局1996年版,第292—295頁(yè)。
⑥陳戍國(guó):《中國(guó)禮制史·隋唐五代》,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任爽:《唐代禮制研究》,東北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
⑦姜伯勤:《敦煌藝術(shù)宗教與禮樂(lè)文明·禮樂(lè)篇》上編《敦煌禮論》“唐禮與敦煌發(fā)現(xiàn)的書儀”、“唐貞元、元和間禮的變遷”,中國(guó)禮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458頁(yè)(后者先收入黃約瑟、劉建民合編《隋唐史論集》,香港大學(xué)亞洲研究中心1993年版)。另外周一良《敦煌寫本書儀中所見(jiàn)的唐代婚喪禮俗》(《文物》1985年第7期,收入《唐五代書儀研究》,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301頁(yè))涉及禮俗也值得注意。
⑧趙瀾:《〈大唐開元禮〉初探》,刊《復(fù)旦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94年第5期;楊華:《論〈開元禮〉對(duì)鄭玄和王肅禮學(xué)的擇從》,刊《中國(guó)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⑨《文苑英華》卷四,中華書局影印本,第3306頁(yè);并見(jiàn)《呂和叔文集》卷五,《四部叢刊》本。按鄭相公為鄭,見(jiàn)內(nèi)藤乾吉《唐六典の行用につぃて》,1936年,《東方學(xué)報(bào)》7,京都,1936年,第118—120頁(yè);收入氏著《中國(guó)法制史考證》,有斐閣1963年版。筆者曾在以往的文章中誤為鄭余慶,特此糾正并感謝武漢大學(xué)劉安志先生指正。
⑩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三《職官》,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98—99頁(yè)。
(11)嚴(yán)耕望:《略論唐六典之性質(zhì)與施行問(wèn)題》,《歷史語(yǔ)言研究所集刊》24,1953年,第69—76頁(yè),語(yǔ)見(jiàn)第73頁(yè)。
(12)見(jiàn)內(nèi)藤乾吉《關(guān)于唐六典の行用につぃて》。奧村郁三《中國(guó)法制史基本資料的研究》,東方大學(xué)出版社1993年版。本文轉(zhuǎn)引自《二十世紀(jì)唐研究》第四章《法制六·唐六典》,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58頁(yè)。
(13)關(guān)于《貞觀禮》制定時(shí)間,《唐會(huì)要》記作貞觀七年,但高明士《論武德到貞觀禮的成立——唐朝立國(guó)政策的研究之一》考證為貞觀十一年。文見(jiàn)臺(tái)灣《第二屆國(guó)際唐代學(xué)會(huì)議論文集》,臺(tái)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9—1214頁(yè)。
(14)以上參見(jiàn)《舊唐書》卷二一《禮儀志》一,第818頁(yè);《新唐書》卷一一《禮樂(lè)志》一,第308頁(yè)。
(15)《舊唐書》卷二一《禮儀志》一,第818頁(yè)。
(16)參見(jiàn)《舊唐書》卷二一《禮儀志》一,第818頁(yè);《新唐書》卷一一《禮樂(lè)志》一,第308頁(yè)。
(17)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卷一《序錄·次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頁(yè)。
(18)陸德明三《禮》中“《周》為本,《儀》為末”的說(shuō)法,與前論《禮記》在二禮之后似有矛盾,與本書實(shí)際排列次序亦不符。王素先生亦解陸意是說(shuō)《禮記》在末(見(jiàn)《唐代文化》第五編第二章第三節(jié),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921頁(yè)),此處疑有闕文,或“儀”為“記”之誤。
(19)《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三,第1266頁(yè)。
(20)《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第1160頁(yè)。
(21)《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影印本,第1222頁(yè)。
(22)《新唐書》卷二《儒學(xué)下·元行沖傳》,第5692頁(yè)。《舊唐書》卷一二本傳“一人而已”下有“莫不宗焉”語(yǔ)。
(23)金子修一:《關(guān)于魏晉到隋唐的郊祀、宗廟制度》,《日本青年學(xué)者論中國(guó)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352頁(yè)。
(24)唐長(zhǎng)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第四章《唐代學(xué)術(shù)思想的變化》第一節(jié)《經(jīng)學(xué)》,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第459—462頁(yè)。
(25)《舊唐書》卷七三《孔穎達(dá)傳》,第2602頁(yè)。
(26)金子修一:《關(guān)于魏晉到隋唐的郊祀、宗廟制度》,載《日本青年學(xué)者論中國(guó)史·六朝隋唐卷》,第345—370頁(yè)。
(27)《唐會(huì)要》卷三七《服紀(jì)下》,《國(guó)學(xué)基本叢書》本,第672—674頁(yè)。
(28)《舊唐書》卷二七《禮儀志》七,標(biāo)點(diǎn)本,第1019—1021頁(yè)。
(29)參見(jiàn)《新唐書》卷二、《舊唐書》卷一二《元行沖傳》,分見(jiàn)第5691—5692頁(yè),3178—3181頁(yè)。以《新唐書》文簡(jiǎn),故引文從焉。
(30)《新唐書》卷五七《藝文志》一,第1428、1434、1441頁(yè)。
(31)《新唐書》卷一九九《王元感傳》,第5666頁(yè)。
(32)《史通通釋》卷一四《外篇·惑經(jīng)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98頁(yè)。
(33)《唐會(huì)要》卷二六《讀時(shí)令》,第491頁(yè)。
(34)《全唐文》卷三四五,李林甫《進(jìn)御刊定〈禮記·月令〉表》,中華書局影印本,第3508頁(yè)。事并見(jiàn)《續(xù)資治通鑒長(zhǎng)編》卷八五載宋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己未龍圖閣待制孫奭上言,指出:“洎唐李林甫作相,乃抉擿微瑕,蔑棄先典。明皇因附益時(shí)事,改易舊文,謂之《御刪定月令》,林甫等為注解,仍升其篇卷,冠于《禮記》,誠(chéng)非古也。”中華書局標(biāo)點(diǎn)本,第1950頁(yè)。
(35)王重民《敦煌古籍?dāng)洝肪硪弧督?jīng)部》,商務(wù)印書館1958年版,第49頁(yè)。錄文見(jiàn)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huì)歷史文獻(xiàn)釋錄》第三卷,斯621《御刊刪定〈禮記·月令〉并序》,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452頁(yè)。
(36)見(jiàn)皮日休《補(bǔ)大戴禮祭法文》,《皮子文藪》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頁(yè)。雷聞《論隋唐國(guó)家祭祀的神祠色彩》指出,皮日休建議將咎繇、伯益、周公、仲尼四人的祭祀直接補(bǔ)入《禮記》原文,也就是將唐代已經(jīng)行用的祭祀實(shí)踐補(bǔ)充進(jìn)儒經(jīng),這一點(diǎn)值得重視。參見(jiàn)臺(tái)灣《漢學(xué)研究》第21卷2期,第114頁(yè)注9。
(37)《舊唐書》卷二五《禮儀志》五,第952—953頁(yè)。
(38)《唐大詔令集》卷六六《祀后土賞賜行事官等制》,商務(wù)印書館1959年版,第372頁(yè)。
(39)《唐大詔令集》卷六八張九齡《開元十一年南郊赦》,第380頁(yè)。
(40)金子修一:《古代中國(guó)と皇帝祭祀》第七章之三《開元十一年の親祭の特質(zhì)》,第230—238頁(yè)。
(41)分見(jiàn)《唐大詔令集》卷一三開元十年五月十一日《處分朝集使敕》,卷一一一開元十二年五月《置勸農(nóng)使安撫戶口詔》,第527、576—577頁(yè)。按前敕據(jù)《冊(cè)府元龜》卷一五八《帝王部·誡勵(lì)三》當(dāng)作“正月”,第1906—1907頁(yè)。
(42)《尚書正義》卷一二,《十三經(jīng)注疏》,第189頁(yè)。
(43)楊華:《論〈開元禮〉對(duì)鄭玄和王肅禮學(xué)的擇從》,第55—56頁(yè)。
(44)《冊(cè)府元龜》卷五八九《奏議一七》,第7038頁(yè)。
(45)參見(jiàn)任爽《唐代禮制研究》,第78—80頁(yè)。
(46)黎斡進(jìn)狀事見(jiàn)《舊唐書》卷二一《禮儀》一,第836—842頁(yè)。
(47)《通典》卷四五《方丘》開元二十年蕭嵩上言,中華書局標(biāo)點(diǎn)本,第1262頁(yè)。
(48)《唐大詔令集》卷六六,第370頁(yè)。
(49)《冊(cè)府元龜》卷三六《帝王部·封禪二》,中華書局影印明版,第396頁(yè)。
(50)《舊唐書》卷二三《禮儀志》三,第900—904頁(yè)。
(51)《舊唐書》卷二三《禮儀志》三,第892—893、899—900頁(yè)。
(52)雷聞:《唐代道教與國(guó)家禮儀——以高宗封禪活動(dòng)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第68輯。
(53)《唐會(huì)要》卷五七《尚書仆射》,第992頁(yè)。
(54)據(jù)《舊唐書》卷九七《張說(shuō)傳》及同書卷八《玄宗紀(jì)上》,張說(shuō)開元十五年曾解免宰相,詔令致仕,“仍令在家修史”;但開元十七年二月復(fù)拜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xué)士,直至十八年十二月病率。因此蕭嵩代張說(shuō)應(yīng)是在開元十九年以后。
(55)參見(jiàn)李錦繡《俄藏Д[,x]3558唐〈格式律令事類〉殘卷試考》,《文史》2002年第3輯,第152頁(yè)。
(56)《舊唐書》卷九九《蕭嵩傳》、《新唐書》卷一二六《韓休傳》,分見(jiàn)標(biāo)點(diǎn)本第3093—3094、4433頁(yè)。
(57)《新唐書》卷一一《禮樂(lè)志》一,第309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