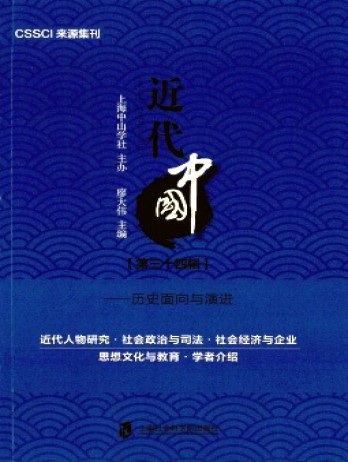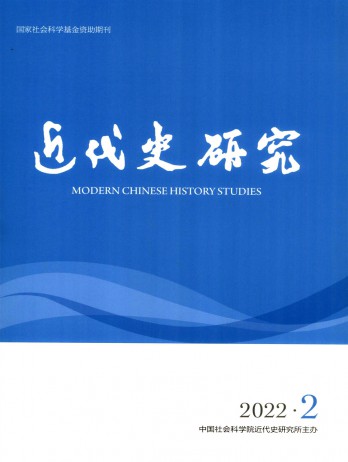首頁 > 精品范文 > 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
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精品(七篇)
時間:2023-06-28 16:51:13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 實驗方法
戊戌時期,實驗方法已經頗受維新思想家的重視。康有為在《實理公法會書》中首先對這種科學方法進行了介紹和應用。他把實驗法稱為“實測”之法,認為這是格致家考明實理的方法之一。在“凡例”中他指出:“是書于凡可用實測之理而與制度無關者乃不錄,理涉渺茫,無從實測者更不錄。”[1] 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科學實證精神。許多西學新知都是因有“實測”之據而倍受康氏推崇,在講學中,他多次向學生指出:“中國人向來窮理俱虛測,今西人(俱)實測。”他教育學生要以科學實證方法批判“清談的程朱”之窮理思想方法。嚴復是近代傳播科學方法影響最大的一人。他在《論世變之亟》中指出,西方富強是因其“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2]。“黜偽而崇真”,即抑虛而尚實,這就是西學實驗方法的要求。在《救亡決論》中,嚴復經過中西文化比較,認定“西學格致”之道與中國相反,西方自然科學講求“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為不易”[3]。在《西學門徑功用》中,他指出,西人“學以窮理”之法門分為三種,即“考訂”、“貫通”和“試驗”,由于“考訂”與“貫通”“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誤,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層,謂之試驗”,“試驗愈固,理愈靠實”。[4] 梁啟超也在《格致之學沿革考略》一文中指出:“虛理非不可貴,然必籍實驗而后得其真,我國學術遲滯不進之由,未始不坐是矣。”[5] 對實驗方法的推重甚至在一些當時制定的學校章程中都有反映。管學大臣張百熙在籌辦京師大學堂時,也強調“泰西各種實學,多籍實驗始能發明”。“政學以博考而乃精,藝學以實驗而獲益”。[6] 當時不少人認為“置器”為試驗之“第一義”,因此親自購置各種科學儀器倡行實驗。如譚嗣同組織的金陵測量會,湊集了天文鏡、子午儀、經緯儀、疊測儀、地平儀、測向儀、羅盤、陸地記里輪、水銀風雨表、量風器、量雨器、量潮器等20多種科學儀器。總理衙門還擬設“儀器院”,要求集中天算、聲光、化電、農礦、機器制造、動植物諸學所必須之儀器,“以為實力考求之助”。當然,維新派雖然對實驗方法很重視,應用的熱情也很高,但真正系統介紹西方實驗方法的書籍尚未出現,國人尚沒有總結出一套自己的實驗方法理論來。
二 邏輯方法
近代中國,早在戊戌維新之前就有人對西方邏輯思想進行過一些零碎介紹。1873年,王韜在《甕牖余談》中最早向國人介紹了培根的生平及學說,但十分簡略[7]。隨后,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譯介了培根的《新工具》,但并沒有引起廣泛關注。直到戊戌時期,嚴復第一個系統地把西方邏輯學引介到中國來,才在中國思想文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嚴復一方面嚴厲批判了中國傳統認識論中先驗理性、唯書唯圣的“圣學演繹”積習,一方面全面介紹了西學中以實證歸納為基礎的科學方法。20世紀初,他還翻譯了西方近代邏輯學巨著——穆勒的《名學》和耶方斯的《名學淺說》,成為近代向中國移植西方邏輯學體系的最大功臣。嚴復把形式邏輯學稱為“名學”,把歸納法與演繹法稱為“內籀”與“外籀”,有時也稱作“內導”與“外導”。他寫道:“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二者即物窮理之最要途術也。”[8] 他又說:“而于格物窮理之用,其涂術不過二端,一曰內導,一曰外導。”[9] 可見,嚴復認為歸納與演繹是科學的兩種基本方法,但實際上他對這兩種方法并不是一樣看待的,受培根、穆勒的歸納主義思想影響,嚴復也偏重于歸納法。他認為歸納能給人提供新知識,能實現認識上的飛躍:“內籀西名inductive,其所以稱此者,因將散見之實,統為一例,如以壺吸氣,引之向里者然。惟能此術,而后新理日出,而人倫乃有進步之期。”[10] 歸納法所概括出來的結論能提供新知識,是人們的具體認識過渡到普遍性知識的一個步驟。所以,“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內籀”[11],“內籀者,觀化察變,見其會通,立為公例者也”[12]。各門科學的公例最初都是由“內籀”而生,“格致真術,存乎內籀,此說固確”[13]。嚴復對歸納法的巨大作用充滿信心,認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上的一切進步都主要是因為應用了此種“格致真術”的緣故。
嚴復對科學歸納法的提倡,其鋒芒是直接指封建經學的。他認為,
嚴復對科學歸納法的具體程序進行了充分闡釋,認為其程序步驟有四層:一是麋集有關系之事實,用觀察法;二是造立“希卜梯西”(hypathesis,即“假設”),用臆度法;三是以連珠等術,推較所臆度者,用外籀法;四是多用實事以校勘所立之例,用印證法。[16] 從這個程序中可以看出,嚴復已經意識到歸納法是與演繹法不可截然分開的。實際情況正是歸納之中有演繹,演繹之中有歸納。嚴復推崇歸納,但并未絕對地反對演繹,他反對的是中國學術傳統中的“圣學演繹”。從總體上看,嚴復把歸納和演繹同樣看作是科學方法,認為“內外籀之相為表里,絕非二途”[17]。甚至說“科學正鵠在成外籀之故”[18]。認為只有運用了演繹才是科學成熟的標志,“學至外導,則可據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時也”[19]。這些思想無疑是很可寶貴的。 康有為也曾傳播和運用過邏輯方法。在《實理公法全書》的開篇《實字解》中,康氏認為西方科學方法有三種:一是“實測”之法,大約相當于實驗法;二是“實論”之法,大約相當于歸納法;三是“虛實”之法,大約相當于演繹法。[20] 該書中,運用以上各種方法的例證俯拾即是,如運用巴黎1891年離婚率等多項統計資料說明“凡男女立約,必立終身之約”不合“實理”,這是歸納推理;而主張“如出自幾何公理之法;則其理較實;出自人立之法,則其理較虛。又幾何公理所出之法,稱為必然之實,亦稱為永遠之實。人立之法,稱為兩可之實”[21]。此為演繹推理。可見,康氏甚至比嚴復更早開始采用歸納法和演繹法來闡述自己的變法主張。
戊戌時期傳播和運用科學邏輯方法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1901年,他在給別人著作所寫的序言中明確指出:“科學大法有二:曰歸納法、曰演繹法。歸納者,致曲而會其通,格物是也。演繹者,結一而畢萬事,致知是也。從現有材料看,這是首先直接使用“歸納”、“演繹”等術語的文字。而且把它們分別與“格物”、“致知”相對應,這是很有特色的。還與嚴復一樣,既認為歸納、演繹都是不可少的近代科學方法,又認為獲得新知主要依靠歸納。他說:“二者互相為資,而獨辟之智必取徑于歸納。”[22]
這個時期,還有章太炎、梁啟超、馬君武等人也重視邏輯方法。章太炎側重于演繹法,他第一個對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印度的因明學和中國的《墨經》之間的異同作了比較和探討。梁啟超將演繹法引進歷史研究領域,強調“綜合觀之”,“有說明焉,有推論焉”,“注意于其來因與后果”,“體悟于百年間若斷若續之史跡”[23]。馬君武則把邏輯學(時稱論理學)稱為“科學之科學”。他在《彌勒約翰之學說》中指出:“蓋各種科學皆須以論理學分析之,查其元素之微,明其聚集之故,究其連合之因,考其組織之序。故論理學者,實凡百科學之科學也。”[24]
總之,經過維新派的努力,包括歸納和演繹在內的邏輯方法最終在戊戌時期比較系統地被引進到中國。此時,除嚴復譯著外,尚有多部宣講邏輯學的譯著先后問世。如王國維譯的《辨學》、林祖同譯的《論理學達旨》、田吳?菀氳摹堵劾硌Ц僖?返取>??廡?韉墓惴捍?ィ?奧劾硌?擠縲泄?冢?環窖?I櫛?緯蹋?環窖д哂夢?卵Х椒ā?25]。
三 數學方法
戊戌以前,中國的算學一直僅以“器”的形式作為“道”的附庸而存在,真正將它提升抽象,作為一種文化的基礎學科和科學的思維方法,則始于維新派。康有為是近代中國以數學方法來闡釋人文理論的第一人。他認為:“天文地理各學皆從算學入,通算猶識字也。”[26] 他鼓勵學生要循序漸進,學好數學。據《康南海自編年譜》載,他自己于1885年即“從事算學,以幾何著《人類公理》”,第二年“又作《公理書》,依幾何為之者”[27]。維新運動時期,康有為在前兩稿基礎上,編成《實理公法全書》,模擬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思維路數,將其認定的人類必須共同遵守的公私關系的道理,分門別類,歸算為若干“實理”,類似歐氏幾何學的“定義”;而把其所設計的為保證“實理”得到遵守的社會生活準則,叫作“公法”,與之作為比照的是各國現行或曾行、將行的信條,即所謂“比例”;還在各論條之下加按語說明,分別相當于歐氏幾何學的“定理”、“公式”和“證明”。康有為這種依“幾何公理”來比擬、推導人類社會進化的做法,雖大有牽強附會之嫌,但卻顯示了這位思想家的大膽思維嘗試和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探索精神。
另外,譚嗣同也是非常重視數學、幾何學及其方法的思想家。他創辦的第一個學會就是算學會。他說,“算法……為格致入門之始”[28],“格致、制造、測地、行海諸學,固無一不自測算而得”[29]。他曾下苦功通讀過《幾何原本》前六卷,還試圖解答其中的疑難問題,認為“算學即不深,而不可不習幾何學。蓋論事辦事之條段在是矣”[30]。和康有為一樣,他也以數學邏輯來建立其哲學體系。《仁學》中的《界說》即模仿《幾何原本》書前的“界說”(定義)制定。例如,界說第十四條“不生與不滅平等,則生與滅平等,生滅與不生不滅亦平等”,即是以代數中的等式原理來推演的。以康、譚為代表的這部分維新知識分子堅信只有數學才是科學的根本門徑,而嚴復則在高度重視歸納邏輯的同時,為數學給出了一個更為恰當的學術定位。他批評了某些國人盲目崇拜數學的傾向,但并未像培根、穆勒那樣武斷地貶低數學的作用。培根“低估了演繹法在科學方法研究中的重要性。演繹法多半是應用數學的,而培根不了解數學在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31]。嚴復沒有沿襲這種偏見,他在《原強》一文中明確提出:“非為數學、名學,則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數。”[32] 可見他是把數學與形式邏輯看作同等重要的。當然,實事求是地講,維新派所接受的數學知識還比較有限,他們反復運用的《幾何原本》到19世紀末也已顯陳舊,而現代數學知識和方法對他們來說又深奧難解,所以數學方法在戊戌時期遠沒有受到前兩種方法的那般重視和廣泛傳播。
四 簡短評價